本篇文章3377字,读完约8分钟
林醒世译《中国近代私人银行的诞生》(日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了聚星城银行旧址
——从现代中国民营银行的诞生看一个例子
沃道
1171年,世界上第一家银行——意大利威尼斯银行成立。1897年,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商业银行成立。1915年,重庆成立了聚星城银行。从时间上看,中国的金融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而西部地区落后于率先开放港口的东部沿海地区。

落后往往意味着根深蒂固的地方思维和强烈的地方属性。这种属性越明显,消化和吸收外部思维就越困难。日本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林兴石解构了中国西部现代民营银行聚星城银行,揭示了中国现代民营企业与现代管理体制碰撞与融合的痛苦。

作为中国西部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民营银行,聚星城银行短短38年的经营历史是近代中国最动荡、战乱不断的时期。在杨家族的领导下,聚星城银行不仅靠寻求财富保险发家致富,还被江浙银行逼回四川。
“危险”迫使军阀们熟练地切割黄金
聚星城银行的创始人是杨,他从江西省东部的南城县(今福州市)来到重庆,但真正的发起人是他的第三个儿子杨。与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父母不同,杨留学日本、美国,对日本“三井财团集中家庭财力办银行、办产业”的商业理念十分推崇。

早在聚星城银行成立之前,其前身“聚星人”就与村民和同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依靠各种帮派的内部联系,聚星人实现了发展和壮大。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银行是“外国商品”。盛宣怀创办的中国商业银行和聚星城银行都是借鉴外国经验的产物。然而,具有鲜明西方市场经济特色的现代银行在登陆西方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水土“调和”的困难。

杨家族有着惊人的分析和判断当前形势发展的能力。杨家认为晚清势在必行,所以他们没有像重庆的其他商人一样避免1911年的战争,而是大肆购买市场上出售的货物和票据,仅这一项就获得了60万元的巨额利润。虽然聚星城银行是在饮过洋墨的杨的指使下成立的,但获得“第一桶金”的“汗马英雄”却是继承其父衣钵的五弟杨干山。

1917年,杨克山得知刚入渝的直系军阀曹锟的旅长李得到100万元的军饷。急于省钱的杨克山积极联系,终于成功赢得了这笔存款业务。杨干山也借此机会创造了一个大的势头。“雇了几十个搬运工,从船上卸下几百万银元,排成长长的蛇阵在城里晃来晃去,吸引路人驻足观看,还有一则广为流传的广告:曹大帅的工资存入了聚兴城银行。”

在强大军阀的支持下,聚星城银行的业务一度平稳。然而,聚星城银行的“第一桶金”似乎来得很容易,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后来的经验充分表明,聚星城银行不仅得益于其与军阀的关系,而且经常被军阀拖垮。1921年,聚星城银行将其总部迁至汉口,这是长江中游的一个交通枢纽城市,但它仍然无法逃脱被军阀强迫接受捐款的命运。1926年,军阀杨森把万县支行的所有员工都绑在县政府身上,要求贷款。"据说每个军阀的贷款总额为150万元."

商业是为利润而生的,它自然会靠“潜力”生存。在军阀混战的时代,社会秩序是支离破碎和混乱的。作为一个强大的机器,军阀的存在自然会成为商人的强大保护伞。然而,军阀的无序和不稳定也为其管理缺乏一致性奠定了基础,这是聚星城银行频繁被军阀劫掠的根源。事实上,这不仅仅是聚集兴城银行被军阀掠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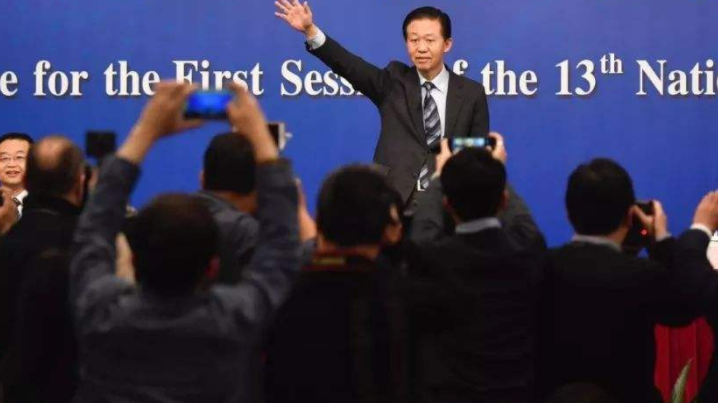
军阀对商人有很大的利益要求,但是他们所能提供的保护是极其有限的。尤其是当军阀自身遭遇巨大的外部压力时,商人很可能成为他们“断腕”自我保护的首选。1934年,刘翔默许了聚星城银行的“银运事件”,但当刘翔受到国民政府的批评和压力时,他突然把枪口对准了聚星城银行。

当时,聚星城银行的命运是其巢下商业和金融业的真实写照,但由于其“大家族业务”而备受关注。
“危险”冲破了中国东部,最终收起了翅膀
重庆因水而诞生并繁荣。聚星城银行得益于码头经济,但随着长江水路经济的蓬勃发展,又经常受到军阀的骚扰,所以聚星城银行离开是正常的。
关于聚星城银行发展路径的争论,不仅是外部环境的推动,也是一场关于“洋派”和“中派”概念的争论。从地理上看,重庆作为中国西部长江航道的重要门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银行业一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现实情况是,“抗战前,东部浙江、江苏两省只有662家银行(包括总行和分行),约占全国银行总数的37%,而西部地区有185家银行,约占全国银行总数的10.32%。”从实际出发,聚星城银行要做大做强,加入东方是必然的选择。

偏偏在这个时候,杨的内部矛盾到了一个紧张的地步。杨不可能指望把三儿子杨送到国外留学,指望他能和兄弟们团结起来变得更大更强,但这是家庭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杨友三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和不同的教育气质。自从开始合作以来,他们在如何扩大家族企业的问题上一直意见不一。杨有发展资本主义集团企业的雄心。而“杨克山长期生活在大陆,带有浓厚的宗法思想,主张以银行业为主体,以巩固家庭基础为重心。双方各持己见,互不让步。”虽然杨克山表面上在董事会选举中失去了权力,但作为创始人,他仍然对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坚决反对将总局迁到上海。在林兴师看来,杨克山态度的根源是“因为他的人际关系达不到上海”。相反,杨是北洋政府与四川关系的产物。后来在抑郁中自杀,这是杨固执己见的结果。

众所周知,商人注意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走出去后,聚星城银行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强的竞争对手,但其规避外部风险(如军阀干预)的能力必然会大大增强。聚星城银行的另一个变化在于它过去依靠地方军阀来接近国家政府。这一变化确实为他们赢得了回报。“战后(抗日战争),它甚至被国民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可以经营外汇的私人商业银行之一。”

在失去了杨对的约束后,强调权力重要性的杨友三变得更加任性决策。1930年,杨爱三在创业初期尝到了“冒险”的甜头,面对冯、蒋、阎三方的战争,认为“蒋必输,蒋介石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必跌”,于是做了一个大“空头”。当江在第一次战斗中失败时,杨澜赚了70万大洋,但他并没有好转。相反,他决定赚100万元,最终落入江浙金融集团和“北方四银行”(中国盐业、晋城、中南和大陆的统称)的包围圈。他不仅吐出了之前所有的利润,还损失了130万元。自那以后,聚星城银行就开始了。

强烈的挫折感迫使杨克山选择了更保守的收缩策略。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九弟杨的带领下,聚兴城银行第二次迁往华东。虽然时代变了,但杨的旧思想并没有放松,最终导致他第二次与兄弟姐妹分道扬镳。
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它从根本上说是老式思维和新思维的对立。以强大的地区关系起家的聚星成银行不容易张开双臂。因此,它不断在区域商业路线和国家商业路线之间以及商业金融路线和工业金融路线之间摇摆。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1937年,在董事会选举的9名董事中,虽然杨家族以外还有6人,但聚星城银行最终代表旧式势力占了上风。

历史不能被假定
聚星城银行的两步走危险游戏不仅是时代的反映,也是其发展理念的反映。
在前一步,聚星城银行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其对人际关系的准确处理。然而,军阀的钱不是那么容易赚到的,它本质上是一个烫手山芋。军阀可以为商人提供保护,包括聚兴城银行,但缺乏外部约束的军阀对商人的要求是无限的。

后一步的危险棋之所以失败,虽然也有“笃定”的成分,但对于杨粲三来说,这一次不一样了。三大军阀混战中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使得长期盘踞在西部的杨粲三难以避免灾难。
正如林兴时所说,“聚星城银行在名义上和实际上已经向西方股份制银行的形式过渡,并一度把国有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事实上,“聚星城银行”在全盛时期并不逊色于中华民国的“四小银行”,如中国贸易银行、思明银行、上海商业银行、金城银行等,因此银行业有“不集聚,不旅行”的美誉。在杨和杨的努力下,聚星城银行在经营机制上力求与西方银行接轨。

从后发优势来看,中国银行在近代似乎曾经有过超越的机会——“中国银行从一开始就采用了现代银行制度”。然而,先进制度能否成功扎根,与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习惯于走“人际关系”路线的传统商人来说,如果建立关系的好处比竞争来得更快、更丰富,他们自然会缺乏专注于竞争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聚星城银行,在社会形势极度动荡的时候,连生存安全感都极其匮乏!
来源:人民视窗网
标题:民国金融家在乱世中的进击与无奈
地址:http://www.rm19.com/xbzx/357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