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3128字,读完约8分钟
哪里有城市,哪里就有人口,哪里就有人口流动。人口流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区域间人口流动规模巨大,且呈上升趋势。作为城市发展最重要的资源要素,人们逐渐被认可,户口门槛也越来越过时。
4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提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并对不同级别城市的结算制度进行了新的总体规划。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城市形成了三种户籍制度。也就是说,城市地区常住人口少于300万的城市应完全取消定居限制;城市常住人口在300万至500万之间的城市应全面放开和放宽定居条件;最受关注的特大城市仍建议调整和完善积分结算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结算。

解放和定居意味着人口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将成为一种趋势,人口流动的原始速度和方向将发生质的变化,城市之间对人口的隐性竞争将变得白热化。
大都市区的外围受益最大
3月18日,石家庄率先在省会城市推行零起点定居政策,取消了此前对“稳定居住、稳定就业”基本移民条件的限制。当地公安部门宣布,只要有身份证和户口簿,就有可能定居下来,从而实现了“有意迁入并与人保持户籍关系”的人口自由流动。

根据这一定居政策的要求,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的二类大城市将完全取消定居限制,因此推测石家庄将很快不再是一个零门槛的孤立城市。
根据《2017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城市地区共有66个二类大城市,常住人口在100万至300万之间,不仅包括乌鲁木齐、贵阳、石家庄、福州、南昌、兰州、呼和浩特、西宁和吉林等省会城市,还包括汕头、珠海、无锡、烟台、常州、佛山和温州等东部沿海经济城市

也就是说,如果国家发改委的文件得到落实,这66个城市将陆续实现人口自由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认为,此举将对中国的城市竞争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城市竞争将从以往的城市间竞争转变为城市群、都市圈、非都市圈和都市圈之间的竞争,分化将越来越大。
根据倪鹏飞的分析,大都市周边的城市可以共享大都市的溢出效应,大都市是农民工的主要聚集地。在宽松的定居政策下,这些城市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
过去的城市发展经验告诉我们,融入城市群是一个城市繁荣和发展的必要条件。40年来,苏州、无锡和常州凭借与上海的紧密联系,获得了发展红利和人口集聚。目前,中国区域经济正从城市化进入大都市发展时代,人口向大都市地区和区域中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

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所和北京清华同恒规划设计院联合撰写的《2018年中国都市区发展报告》确定了34个都市区,分别占总面积的24%、总人口的59%和国内生产总值的77.8%。
此前,许多专家呼吁改革户籍制度,允许人口在大都市区自由流动。这次发布的户籍制度改革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对这一要求的部分回应。对于大都市地区的二类大城市(100万至300万)来说,下一步是如何利用免费户口的优势吸引中心城市的流动人口并分享发展红利。

然而,倪鹏飞也指出,取消户口障碍并不意味着没有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而是取决于如何在当地实施,否则在社会保障、就业和住房保障方面仍然会有阻碍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
中心城市:抢人与解决并重
2018年至今的城市“抢人战争”为户籍改革铺平了道路,人口取代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观念的天平正在倾斜。
然而,表面上的“人才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竞争”,因为大多数城市都注重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才。
中国城镇改革与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认为,这种城市人才准入标准仍然存在很强的短视行为,忽视了更具活力的符合城市就业需求的农民工,实际上放弃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机遇。因为要衡量一个城市的扩张和发展,更重要的是看第二代和第三代。一个城市的活力取决于年轻人口和后代的教育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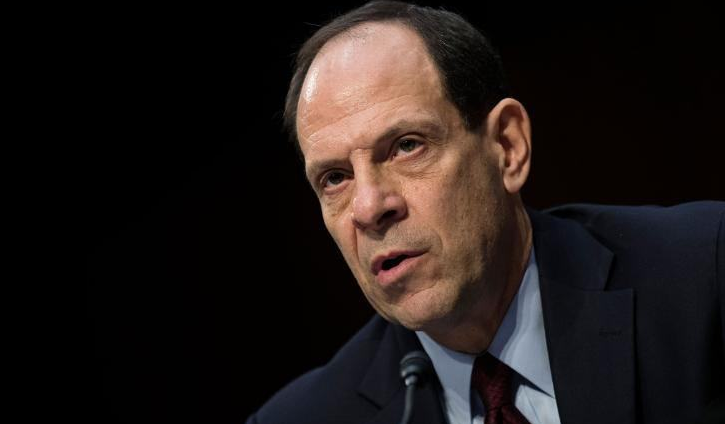
对于常住人口在300万至500万之间的一类大城市,户籍改革规定,定居条件应完全放开和放宽,对重点群体的定居限制应完全取消。文件中的“重点群体”是指在城镇有稳定就业和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生活5年以上并随家庭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以及上了大学参军进城的农村学生人口。

显然,他们是对家庭改革有最强烈要求的人。根据2017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考虑到2018年的人口增长,这些城市并不少见。
然而,在NDRC文件中有针对性地表达“关键群体”可被视为政策层面上的“拨乱反正”。
倪鹏飞认为,更自由的人口流动将更有利于这些城市抢人,但前提是这些城市要做好人口救助工作。不仅是特大城市,一些特大城市的中心城市的人口也已经人满为患,出现了明显的“城市病”,需要向周边地区缓解。只有将人口分散到周边地区,形成跨区域的人口协调发展,才能吸引更多的移民,形成足够大的市场,支持中心城市的转型升级。

以一线城市为例,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呈净流出状态。2018年,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分别减少了16.5万人和3万人。然而,由于广州和深圳实施相对宽松的户籍政策,常住人口仍在大幅增长,2018年分别增加了406,000人和212,000人。

一方面,它是一种大城市病,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更宽松的户口政策,大都市地区被赋予了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任。
当然,人口流动性的关键不是户口本身,而是与之相关的公共服务。解决的关键在于工业和公共服务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否则,更多的定居将带来更严重的城市疾病。
边缘城市将加速收缩
一些城市的人口数量正在增加,这意味着其他城市的人口数量正在减少。2018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至3.81‰,人口红利消失,总人口如此之大,人口必然会发生变化。
此前,在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政策下,人口积极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平衡战略的相继实施,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得到了发展。然而,这种区域性政策无法改变一些中小城市的命运。

北京经贸法副教授吴康(音译)曾经画过一张地图,其中一个黑点代表一个“正在缩小的城市”。在地图上,中国东北的黑点已经连成一条线。但是,应该指出的是,除了区域经济整体崩溃的地区外,即使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黑点也出现了碎片。

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学者应龙认为,一些城市的“收缩”是城市生命周期发展中的自然现象,特别是在过度依赖矿业、林业和石油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而一些城市的“收缩”则是城市化的结果。
根据龙鹰的统计,在2007-2016年期间,中国有84个城市经历了“收缩”现象,所有这些城市的常住人口都经历了连续三年或更长时间的下降。
随着大城市户口的开放,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两极分化”效应,这将加速人口向大城市的迁移。距离中心城市太远的边缘城市无法逃脱“收缩”的命运,取消户口限制将加速这一进程。
倪鹏飞分析说,完全取消定居限制后,人口流动将更加市场化。就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水平而言,远离城市群和大都市地区的城市无法与城市群和大都市地区的城市竞争,自然对人口没有吸引力。这些城市将面临人口要素的自然流失,竞争力将越来越弱。

退缩不是一件坏事。应龙认为,关键是每一个萎缩的城市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规划,追求精明的收缩,而数量的收缩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收缩。相反,萎缩的规划应该更加注重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城市质量。
在本次发布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也首次提出了缩小中小城市的提法,强调中小城市要转变惯性增量规划思维,严格控制增量和盘活存量,引导人口和公共资源向城市集中。
对于习惯了“摊大蛋糕”发展逻辑的当地政客来说,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过去,各种管理城市的经验和手段都将是完全无效的。面对持续的人口流失,城市该如何运作?
来源:人民视窗网
标题:去户籍时代下的城市竞争:都市圈内外强弱分化
地址:http://www.rm19.com/xbzx/31688.html

